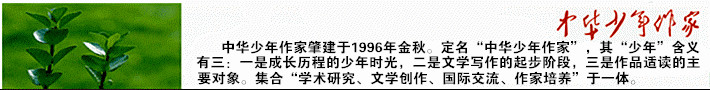2015年,移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薛忆沩一口气同步出版了五本书,其中访谈录《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率先面世。同时,由三联书店重磅推出的“薛忆沩文丛”三版也即将上市,分别是《文学的祖国》(新版)、《与马可·波罗同行》(新版)以及小说精选集《与狂风一起旅行》。
薛忆沩今年51岁,身上贴着“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标签,自认近三十年独立于主流和传统文学之外,走了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
访谈录中,薛忆沩将其写作生涯中应邀所写的各类访谈文字重新梳理后一一呈现。将对话的主语、宾语“兼并”成同一个人后,薛忆沩“捏造”了这本访谈录的书名。书中,首篇虚拟访谈《薛忆沩采访薛忆沩》与书名一脉相承,由薛忆沩对镜而坐,自问自答:“我试图借用这种蕴含‘自传’元素的文字游戏,不断对自我、人生、文学、历史等重要命题展开追索和反思。”
1994年,薛忆沩以一部《遗弃》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同届获奖的还有王小波和他的《黄金(1164.10, -2.10, -0.18%)时代》。1997年,现为北大哲学教授的何怀宏在周国平家里看到了这本书,当即惊艳,随后在《南方周末》上大力推荐。这是薛忆沩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遗弃》被认为提供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样本。何怀宏将薛忆沩的探索称为“寻求永恒的最初一段旅程”。所谓“最初”,并不仅仅因为作者与主人公异常年轻的年龄,在这样的年纪,虽然看似离永恒、死亡这样的话题最远,却也常常是能够捕捉到死亡黑影并隐秘渴望永恒的最初阶段。“最初”的另一层含义是,文中的“我”与世界之间的互弃,这种看似极端空虚的生活状态恰恰是对庸常人生的激烈反抗,而这正是“寻求永恒”的最初旅程。
完成《遗弃》时,薛忆沩24岁,在那样的年代,以这样的年纪,鲜有小说家会把“内心的奇观”作为描写的对象,对此,薛忆沩以福楼拜作比:“福楼拜说是他的人物选择了他。我也想说,是我的描写对象选择了我。在我看来,写作者不仅是语言的奴隶,也是自己描写对象的侍从。‘内心的奇观’从来都是我的对象,是我所有作品的对象。我总是说文学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看见‘看不见的城市’;‘内心的奇观’就是‘看不见的城市’里的‘地标’。”
薛忆沩在小说里描写“看不见的城市”,在现实中则在一个个现实的城市中不停迁徙。北京、湖南、深圳、蒙特利尔,“异乡写作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情。”他诚恳地说。
漂泊越久,薛忆沩越相信所谓“宿命”。1983年,话剧《推销员之死》第一次在中国上演,彼时尚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的工科男薛忆沩不仅拿到了门票,还坐在了曹禺、丁玲以及亚瑟·米勒的旁边。薛忆沩把这件事当成某种启示,由此声称文学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宿命,作为被“上帝选中的作家”,他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当成了写作的“祭品”,在一意孤行的冒险中,兑现与文学的“神圣之约”。
观察,抵达生活的核心
记者:你怎么评价外界称你为“中国文学的异类”?
薛忆沩: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我就是自己而已。我追求的是文学上最正宗的那些观念,比如对人的看法、对人的悲悯等。“异类”会让人以为此人是放荡不羁的,而我在写作、运动、生活上都是特别严守纪律的。
记者:你自认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吗?
薛忆沩:对,现在我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我习惯在历史里面发现个人,从人性的、常识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去观察历史中到底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这很让我着迷。
作为一个作家,对细节的把握也是天赋的能力。当我看到公交车上的两个人,我就知道接下来的10分钟里,这两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果然发生了。看过往的行人,听他们讲话,就可以接触到生活最内核的东西。与之相反,社交往往是最肤浅的。有朋友说我几十岁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他们可能是觉得我不世俗,而我自己觉得,只有心灵纯净时才能善于观察别人—孩子是特别有洞察力的,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
但是,文学不可能只靠自然的流露,写作需要不停地练习、打磨,才能由不自觉走到自觉。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艺术的美高于自然的美,要练习,同时保留一种纯真的状态。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而是几十年、一辈子要做的事。说得简单一点,要达到那样的境界,需要的是“实践实践再实践”。简练和精准其实是一个复杂又神奇的认知过程,它经常会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有一种“成事在天”的感叹。
迁徙,思考个人与祖国的关系
记者:生活中,你是一个经常改变生活地点的人,这样在外界看来“动荡”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薛忆沩:迁移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后,最重大的改变来自语言上的感觉,因为英文的参照来了,我就更加注意到了汉语精确的那一面。我发现其实汉语很有逻辑,以前别人总说汉语没有逻辑,我自己也这么说,但是汉语完全可以做到很有逻辑,就看你怎么做了,要很用心地对待它才行。
生活在异域,也让我重新思考个人与祖国的关系。我的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重点讨论的也是许多写作者都遭遇过的问题:地理上的祖国与文学的祖国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思考一直延伸到了我的虚构作品之中: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里专门有一段关于“祖国”的讨论;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祖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我其实很早就注意到迁移在我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964年4月,我出生于湖南郴州资兴煤矿的矿区医院,四个月之后就随父母迁回了长沙。在17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虽然一直在长沙生活,却有多次和多重的搬迁经验:比如从城市的北区搬到靠近城市东部的郊区,又从靠近城市东部的郊区搬到了城市的南区;再比如从具有悠久历史的校园搬到了国营工厂的生活区,然后又从工厂的生活区搬到了另一所没有什么历史的校园。这些搬迁为我打开了一个一个的“世界之窗”,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形态。
我觉得异乡写作是百益而无一弊的,异乡流浪产生的距离感,能够让你去清理自己的记忆。这是很好的,很多感觉都保存在你的记忆里。
记者:外界认为你的作品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大,你认同吗?
薛忆沩:其实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西方语境的环境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的。但是,中国文学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很小就读过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1975年年初,我父亲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他带我去住过几天。我从那里的图书馆里借阅了《三国演义》,稍后又突然爆发了评《水浒》的政治运动。虽然“权”“谋”“侠”“义”等统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主题从来就无法打动我,但是作为一个敏感的孩子,我不可能不为“情”所动。《红楼梦》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在改革开放后长沙的第一次书市上,我最重要的购买就是一套《悲惨世界》、一套《红楼梦》。《红楼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它的智慧、情怀、忧郁都在我的意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迹。这种印迹也许深入到了“无意识”的层面,偶尔会在我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
西方文学影响我最多的是乔伊斯和卡夫卡,这两位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们对语言和结构的重视、对写作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激情,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在乔伊斯的作品里读到了语言跟事物之间的完美配合,非常精准。卡夫卡对我的影响则更多是形而上的、哲学的,他连故事结构也是形而上的。
记者:《遗弃》是你24岁时候写的,48岁时你又重写了这部作品,为什么?
薛忆沩:多种语言的冲撞导致了我对汉语的崭新感觉。在2007年前后,我重读自己的旧作,这种感觉让我很容易就发现了作品中的许多破绽,我无法容忍那些破绽,于是从2010年开始重写旧作。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年。我的重写尊重原来的故事和情绪,我的重写带来的主要是语言的流畅和细节的丰满。
记者:你和村上春树都是喜欢长跑的作家,对你而言,长跑意味着什么?
薛忆沩:我喜欢长跑,长跑带来一种踏实的疲劳感,可以缓解写作带来的压力,其实就是给自己充电,顺便锻炼身体。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高扬)
责任编辑:文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