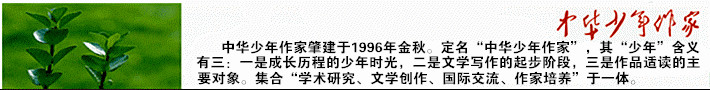◎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E.B.怀特
“一个作家应该关注任何让他浮想联翩、让他心潮澎湃、让他的打字机进入状态的东西。我没觉得自己有关心政治的义务。我的确感觉到对社会有一种责任,因为我在出版东西:一个作家有责任尽力而为,不滥竽充数,力求真实而不作假,生动而不乏味,准确而不谬误连篇。”

科塔萨尔
“我对自己要求很严,现在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些同辈人刚刚写出一些诗,或者一部小型长篇,马上就寻求发表。我告诫自己:‘不,你别发表,继续努力吧。’有些作品我留下了,其余的被我舍弃了。当我首次发表作品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正是我动身去巴黎之前不久。”

诺曼·梅勒
“现在我们很困扰。都是电影的错,尽管美国作家一直以为我们在好莱坞方面要略胜一筹。可是你不可能从电影里了解到多少人性,你只是去娱乐而已——完全浪费了你追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和能力,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诸多麻烦之一。”

唐·德里罗
“我上午用手动打字机写作。大约写四个小时,然后去跑步。这帮助我从一个世界抽身而出,然后进入另一个世界。树、鸟和细雨——这是很好的插曲。然后我下午继续工作,写两三个小时。回到读书时间,这一段是透明的——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度过的。我不吃零食,也不喝咖啡。不抽烟——我早就已经戒烟了。屋子空间很大,房间也很安静。作家会寻找各种办法来确保自己的孤独,然后再寻找无数方式来浪费它。”

大江健三郎
“诺贝尔奖对你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为社会人物的地位。你获得某种货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使用。但是对作家而言,什么都没有变。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没有变。只有几位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继续写出好作品。托马斯·曼是一个。福克纳也是。”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
作者:《巴黎评论》编辑部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11月
2013年,《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创刊60周年,《新京报》在该年十一月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赞誉这本老牌的文学季刊的作家访谈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持久的文化对谈”。
作家们用这本书取暖
与第一辑相隔三年出版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作序的帕慕克也是访谈的铁杆粉丝,以“宗教典籍”譬喻之,受访的诸位作家,文学的先行者无异成了圣殿里的诸神。他设法找到每一卷《巴黎评论》,在其中受启蒙与启发,在长久的孤独写作生涯与他们相濡以沫,甚至领悟出“厌恶庸常的普通生活原来不是一种病,而是智慧已开。”
是的,热情与智慧,帕慕克点出了与《巴黎评论》画上等号的作家访谈此一专栏的关键字。因为热爱文学与作家,深刻了解书写创作这一古老手工艺的旷日费时,却常常一事无成,了解他们的异常是一颗颗始终发热的心、一双双所见不与人同的眼睛,《巴黎评论》的访谈建立了一套看似最普通的作业方法,先读遍受访者的作品,熟悉其生活与生平,且不企图只一次访问便收网完事,譬如冯古内特的四次访谈跨时十年,麦克尤恩则前后跨越五年的时间;看似最朴素的问答形式,《巴黎评论》如同虹吸管,源源引导出作家的写作观、世界观、如何品人以及诸般爱憎好恶。虽不至于让我们读者好像看鱼缸里的金鱼,但也足够有一览无遗的效果。这也是为何帕慕克自承屡屡从作家访谈取暖,让他一再找回写作的信念,也私淑偷学了很多小说技巧。
第二辑一共一十六位作家,创刊号的E. M.福斯特开始,以大江健三郎(刊登于2007年)压轴,囊括了赫胥黎、博尔赫斯、E·B·怀特、斯坦贝克、品特、聂鲁达、唐·德里罗、桑塔格、诺曼·梅勒;不管是出于作家天生的丰沛同理心,或者对于时潮风向的敏锐掌握,其中一二更是国际知名的政治人物。在《新京报》2013年底的那篇访问,《巴黎评论》的回答揭示了其独特视角:“专心经营作家访谈这个特色板块,就是为了让创作界的内行来公布行业秘密,揭示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家生平与创作的关系,抵御来自于‘批评’的审视。”
行业秘密?这真是有趣了,要让出入于现实与虚构已成职业惯性的第一流作家据实说出内心话,岂是易事?然而写作不就是极端个人的心灵思维,一切灵光来自专注、长期不懈地思考,哪来的这么多像武功秘笈那样的秘密?
读者们获得阅读红利
是以,《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的确就是那一句老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写作同行,如同帕慕克的比喻,来到坛前听道、听证词般具有宗教(或是秘教?)意味;对于认真的读者,隐藏书后的作者现身了,近距离或能让他们的书更立体,让阅读更深层吧,仿佛资深导览随行的深度之旅。
我们当然也可以将这一十六位举世闻名的作家访谈视为写作技艺或诀窍的经验交接,然而,归纳出来的准则其实比我们预期的少很多,也平淡无奇。譬如,作家的写作时间大都是在早上,规律的每日书写,并不要求深山古刹那样的安静,嘈杂的咖啡馆他们照常工作。几乎每一位都这样捍卫写作的尊严与荣光:不,工作的时候我很少、甚至不会想着读者,“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当我把注意力放到打字机上时,脑子里压根不会想象什么读者。”
就在他们背向读者时,我们才发现作家访谈这个系列是文学共和国的阅读红利。我们因而更确认了博赫尔斯的睿智、亲切,苏珊·桑塔格的自负,冯内古特的搞笑个性,也发现了聂鲁达的爱热闹,唐·德里罗有跑步习惯,硬汉诺曼·梅勒相信转世投生。
毕竟好作家握有更多坦承表白的资本,当艾萨克·辛格说:“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江健三郎这一段如同夜深私语,自我解除了作家的神圣光环,可说是最动人的自剖,“我并没有信仰,我也不觉得将来我会有,但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信仰是一个俗世之人的信仰。你可以把它叫做‘道义’。一生中我获得了某些智慧,可一向只是通过理性、思考和经验。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俗世之人的生活方式,而我就是那样来了解人类的。”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安黎)
责任编辑:文禾